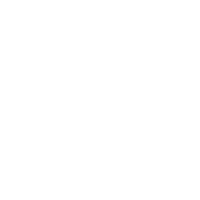師者如蘭,曆之彌久,幽香愈馥。探路之如履薄冰,行路之矢志不渝,領路之循循善誘;一路栉風沐雨,方得稇載而歸。他們深深淺淺的足迹正可為上下求索的學子指明前行的方向。
近年來,有多位青年教師加盟伟德这个平台怎么样行政法研究所,他們有着不同的學術背景,有着不同的研究領域,但對年輕學子們卻有着相似的關切,對三尺講台更懷着共同的熱愛。本欄目秉持“法治天下,學問古今”的院訓,将首先邀請他們參與訪談,取其鑽研學術之經驗,勤懇育人之情懷,暢言于一室之内,與廣大學子共享。
本期欄目嘉賓為伟德这个平台怎么样教授、博士生導師趙宏老師。趙宏教授1999年畢業于伟德这个平台怎么样 獲法學學士學位;2002年畢業于伟德这个平台怎么样,獲法學碩士學位;2005年畢業于北京大學獲法學博士學位,期間作為交流學生赴德國圖賓根大學學習一年。主要研究方向為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,精研方向為基本權利教義學,行政法基礎範疇,國家法與國家學。
問:您多次前往德國交流,是否在本科階段就有前往德國的打算并為此學習德語?
當時我學德語的時候,一開始并沒有清晰的學術規劃,沒有把德語特别清晰地跟自己的學術規劃聯系起來。隻是在讀研二的時候,因為學校要求學第二外語,我就選了德語。但我對學習做事一向都比較上心,所以在課程之外也想再深入地學習德語,于是就在研三時又去北外報班學習德語。但是博士期間去德國進修是很巧合的事,當時我在北大讀博,德國的Hermann-Hesse基金會給了北大伟德这个平台怎么样兩個名額,但是在選拔的時候,發現北大伟德这个平台怎么样隻有兩個人學過德語,所以就選定由我和另一個同學去德國交流學習了。所以這件事也告訴我,任何學習都不會是浪費的,都會在人生的某個時刻給予你回報。
問:您覺得在德國學習的經曆對您的教學科研工作有什麼影響?
德國學習經曆對我的最大啟發,就是德國法所倡導的是法教義學方法,即對規範進行解釋,通過解釋把規範塑造成邏輯自洽的一個整體,同時讓規範面向這個社會生活,帶有一定的開放性,能夠用來解釋和指引外部世界,這種全新的教義學的思考方式帶給我很大觸動。
因為在我求學的那段時間,大部分老師的授課方式還是批判法學的方式。最直接的體現就是不太關注法條和規範。老師上課的時候,跟現在的上課方式也完全不同,不涉及法條,老師講的更多的是理想中的法律或書本中的法律,偶爾講到法條的時候,老師也更多是以批判的态度。這也直接導緻我們在學習的過程中,也是不關注法條的,我們隻是學習書本上的比如說概念、原則、理論、分類、意義、功能等。這就導緻我們對法條不親近,也不知道法律的世界其實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是由法規範來運作的,而這個法規範又是通過一系列的——比如說法律解釋的方式、法教義學的方法搭建起來的。
因為德國法的影響,所以我在上課的時候也會強化對法規範的分析和理解,強化法教義的方法。我上學期講課結束後,有一個學生的課後反饋,讓我覺得震動很大。他說以前聽行政法,老師基本都是批判式的,會講行政法存在的諸多問題。因而留給他的印象就是這個學科問題太多,以我個人的力量也沒辦法拯救,所以幹脆放棄好了。但我在給他們講課的時候,在講到比如說行政處罰法、許可法、強制法,或者講到複議法、訴訟法時,我都會要求大家首先理解和分析規範,然後再講法律原理,思考法條之間邏輯關聯,以及如何去解析一個法條,這個法條和現實案件又如何關聯。
所以這位同學反映在聽我講課的過程當中,覺得行政法還是像法的,不像大家以前所認為的隻是一個行政管理的規則的彙總,相反,還是有法律的意涵和内容的。另外他也覺得老師如果不是一味地批判法律,而是告訴我們法律為什麼要這麼規定,它們中間的邏輯關聯、意涵要素的時候,他反而覺得法律裡面值得挖掘的東西其實還是挺多的,于是也覺得這個學科還挺有意思的。我覺得我之所以能夠給他帶來這樣的感受,可能也是因為我受到了德國法的影響。
問:您曾經也在科隆大學開設過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,對比來看,您在中德的授課經曆有什麼相同與不同之處呢?
我在國内講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,所面對的學生是已經接觸過法律,有一點法律基礎的。我們的講課方式也基本是按照中國學生的學習習慣設定的。中國學生的學習習慣基本上還是将知識系統化,體系化,例如說從概念、原則、分類、功能入手,在這裡面再加入一些案例的讨論,或者規範的解釋,包括法規範的社會效果反思等。可能因為講的時間也比較久,所以覺得難度其實還不是那麼大。
但是我覺得去德國講課的經曆是完全不一樣的,因為它的課程設計主要以學生讨論為主。而德國學生的關注點,和中國學生的關注點又不太一樣。比如說我當時為了講這個課,做了很多的準備,包括把我的講義全部都翻成德文,然後按照中國的方式做德文的PPT,重寫講義等。但後來我發現講的過程當中,他們不關心概念、原則,更關心一些具體的數據,比如說他們會經常問我:老師,在中國哪個機關會最經常成為被告?或者在哪個領域當中發生的行政案件是最多的?他們會特别關注這種數據的問題,想要你給他們提供比較細緻的數據分析,他們可能更信賴數據的反映,而不是原則性地講授的法律原理。
問:您如何看待自己未來的工作?
我對未來做的一個基本的設定是,首先要做好教師的本分。我希望我未來可以花更多的時間做學生的培養,我常常想自己的工作就像是捧着知識的火種,我也希望可以經我的手,慎重地把知識的火種傳遞下去。我也希望自己未來能夠在講台上探索更多的授課的可能,讓自己的授課或者是私下裡跟學生的互動可以更多地影響到其他人,能夠把我學了這麼久的法律所接受的訊息和感悟持續地傳遞下去。老師其實就是知識鍊的一個部分,而我也希望自己能夠起到知識傳遞的作用。
攝影丨羅旭輝
采訪丨吳泓瑄